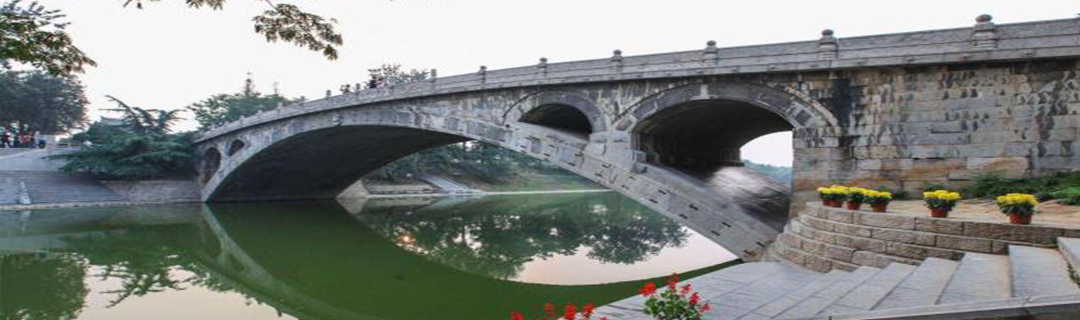一、如何理解“案结事了”?
按我的理解,所谓“案结事了”,就是指凡是经过人民法院受理的或审理过的案件,当事人不再对同一个事由提出任何诉求,包括对法院,包括信访以及其他机制。就是说它主要是同一事由,或者同一事件,这个应该作为事了的一个标志。也就是同一个事情,同一个事由不再提出任何诉求。如果说当事人对其他的事情提出诉求,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案结事了还是要回到法院对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上来理解。一个是受理案件,一个是审理案件。比如说,法院受理了案件,并且经过审理后做出了裁决,裁决了也是案结了,也就是事了了。凡经过判决了,裁定了,都属于此,当事人不再就同一事件提出诉求。当然,还有一个诉讼机制问题。法院所作的裁决应该把它理解为终审性的,带有终决性的裁决。比如对于一审判决,当事人提出上诉,你不能说事了了,因为这是个诉讼机制。所以谈案结事了的这个“案”,应该是终审意义上的、终结意义上的处理结果,然后当事人不再就经法院受理或审理过的带有终决性质的决定提起任何诉求,这就是我对案结事了的一个理解。
二、应该建立法院系统的案件终结制度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和案结事了问题相关,就是能不能在法院系统搞一个诉讼案件终结制度?什么意思呢?其他领域的事法院管不了,但是法院对它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对于终决案件、终审案件,包括经过申诉或再审的案件,能不能在法院系统内部终结,就是不再受理。别处的事法院管不了,但是在法院系统,案件已经了了,已经结了,就再不受理了。这个制度如果建立起来,至少可以解决法院系统内的这个无限制的不间断的上访、信访。当事人到别处去信访、上访,法院没办法,比如有上级转来的信访案件,还有上级指定的复查案件等,对于这些,法院没有办法。但是法院系统的案件终结制度如果能够建立起来,至少可以提高法院的权威,实际上也是提高司法权威的一种方法。也即对于法院来讲,该穷尽的渠道已经穷尽了,法院的司法程序已经穷尽了,当事人也穷尽了,大家已经做到最大程度了,如果当事人再就同一事项无限制地不断地上访、信访,那就是已经离开法院诉讼程序的这个渠道了。但是难处就是法院的外部环境管不了,上边压下来的怎么办?法院实际上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法院有终结制度,已经终结了,案件已经终结了。因为当事人的诉愿你无法去限制,当事人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诉求,你无法左右。但是在法院的范围内,只要我们认为,法院在程序里面该利用的已经都穷尽了,当事人也穷尽了,法院也穷尽了,就可以了了。这是关于案件终结制度。当然,我这个想法可能有些天真。因为法院不受理,当事人可以到人大去,到信访局去,到其他部门去,信访局又会反转到法院,人大也会反转到法院,怎么办?那么,如果这个案件终结制度做的有道理,法院可以以这个制度作为抵抗的,就是从制度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国家也在研究信访终结制度。没有一个终结,司法权威就树立不起来,对终审判决的权威还是要维护,只要是符合程序性的,这就是法治,不然什么叫法治。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三、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不是一个主观感受而是一个需要依靠客观数据说明的问题
这几年法学界研究的“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是与“案结事了”相关的一个问题。我指导的两个博士后,有一位研究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还有一位在研究民事判决理由的可接受性问题。我们过去对于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常常会把它看作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不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由客观数据来分析说明的问题。比如一审的服判率,上诉率,一审的执行率,还有撤调率等等好多指标体系。我那位学生做了20多个表,他把1988年到2011年全国的案件情况做了分析,做了比较,数据分析下来的结果和我们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现在觉得司法权威不高,但他经过数据比例分析,发现我们现在的一审服判率,自动履行率,自动执行率等,要比过去高许多。我后来对他说,仅凭数据比例分析是有漏洞的,漏洞在什么地方?就是案件基数不一样,过去比如说100个案件,现在1000个案件,从比例上看,现在的一审服判率、自动履行率在提高,但实际上,基数不一样,总数字可能还是在发生变化,就是说只靠一个比例,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当然,比例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从他的研究报告来看,我们现在的比例情况要比过去高很多,但是我们感觉司法权威越来越不行,这当然需要做很多分析工作。
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包括事了,关键是建立一个什么标准。这个标准是按照司法标准来判断,还是按照当事人的标准来判断,这是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认识事了?事了的标准怎么来确定?比如说一审结束后,不上诉了,它不再二审了,那就是说至少判决结束了,然后又自动履行了。那至少在我们看来是事了了。如果他再就同一个事项,事后反悔了,事后再通过其他途径提出诉求,那个是不是属于事不了的范围,这个要推敲。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司法标准,还是当事人标准。在事了的问题上,如果标准不一样,分析结论就不一样。当然,现在事不了可能主要指的还不是这一块,可能指的是不自动履行的,履行不了的,或者就是说不断地要申诉的,不断地上访的,是不是指的那一部分?还有比如说申请强制执行的,强制执行如果作为一个法律程序,算不算事不了,这个都需要思考的。如果说法律规定了强制执行,判决后对方不履行,另一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一直有一个认识,只要是诉讼程序范围内的,都是法院职能范围内的事,就不能轻易的给它往外推,即应该把它看做一种没有解决问题的结果。比如说,强制执行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执行程序,提出强制执行也在法律之内。至于说强制执行的决定下来之后,还执行不下去,这个怎么来看。至少把强制执行不能算事不了。对于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可能很多人的认识还没有转过来,还是把它看做是一个主观性感觉的问题。很多人研究这个问题时很简单,就是当事人算一方,法院算一方,然后社会算一方。拿出了社会这个概念。社会这个概念很复杂。一个案件会引起社会的很多的讨论,对案件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映,能不能作为判断案结事了的一个事由,或者标准,或者能不能作为事不了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判决都具有合理性,但我们应该兼顾到司法程序、判决的权威性。我们这些年对社会民意的这个因素大大超过了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权威性。 我仔细研究过民意这个概念。在司法里面,谁能代表民意?谁的意见能代表民意?张三的,还是李四的?因为民意这个概念,应该是民主制度的产物。非经民主程序所达成的意见,很难给它戴上“民意”的帽子。包括社会舆论调查。社会舆论调查能代表民意吗?有些人用数量来判断,在讨论“我爸是李刚”那个案件时,有人说有四亿人跟帖,我说数量能说明问题吗?我们是靠数量来判断一个问题,还是靠真理性来判断问题?当然,数量有时候不能不考虑,但是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靠人多人少。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包括我刚在上海参加的一个会议,有一篇文章也是研究社会对判决的可接受性。社会对判决的可接受性怎么判断,是不是网络舆论对案件反映强烈的就是不接受,这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一直没有解开的结。司法中关于社会舆论也好,关于民意也好,对司法到底起多大影响,这个影响到底怎么看,这个结还没解开。而且,司法中,民意是一个虚妄的概念,是一个没法证实的概念,谁代表民意?没法回答,网络一片攻势下是不是就代表民意?且我们要看到,民意是随时变化的,成都的那个孙伟铭案件,醉酒驾车撞死四个人,一审过程中民意全部在谴责他,强烈要求严惩。法院一审判死刑后,舆论又反过来一边倒,又同情他了,最后,二审判了个死缓。二审的判决是否受了舆论的影响,我不好做判断,因为没法证实。但是,很多人都说,包括李昌奎案件,是民意取得了胜利。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个案件如果有明显的错误,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舆论攻势,是不是就不会改变?这种案件的改变是它本身应该如此,还是由于强烈的舆论攻势?当然,有些案件比较特殊,像张金柱、刘涌案件都是拿来作为例证的,都是大的案件。判决的可接受性,案结事了,以及舆论的影响,它们之间都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还要谨防舆论的被操纵问题,舆论被操纵的几率也非常大。有时候媒体要想操纵一个事情完全可以办到,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对于案结事了而言,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当事人基于同一纠纷或类似纠纷反复诉讼、重复诉讼。这个反复诉讼,重复诉讼,恰恰是我们在法律机制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法律能不能对这种现象做出规定,这是诉讼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还有少数法官为了片面追求结案率指标,在结案高峰到来前,动员当事人撤诉,这个在全国法院都是一个不言的秘密,就是在年底前,基本上不受案,然后积压到第二年。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也发了文件要求纠正,但还是制止不住,法院的绩效考核制度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是要在制度结构方面解决问题。